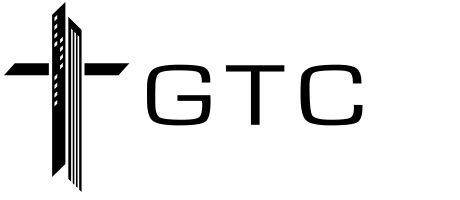城市植堂运动DNA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共识,有助于我们彼此联合,同时它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在不同文化、国家和城市处境化地应用与实践。这常常需要我们平衡特定主题的具体指导与变通之间的关系。公共神学可能是其中最难找到平衡的主题之一。在讨论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时,很容易变得过于教条或不够具体。
一方面,圣经教导基督徒必须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参太5:13-16;彼前2:9-12),使世人能看到我们爱邻舍,并致力于公共利益。这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我们也(门徒)训练教会成员“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10:31),使基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居首位(参西1:18)。这意味着基督徒当照着圣经的教导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和权利。教会有责任教导基督徒如此行,这就是公共神学。
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都不一样。例如,有人可能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很相似——英国的工党与美国的民主党类似;保守党与共和党类似。但实际上它们不完全一样,有些人甚至认为其差异远多于相似之处。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能够理解“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概念,在城市中更是如此。但在不同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所关注的具体议题往往差异很大。
因此,本章的目的是将公共神学这一议题纳入城市植堂运动的“地图”。过去,我们很少讨论公共神学——即使讨论了,也只是在文化参与这一主题中稍微提及。我们能否在服事普世教会的层面探讨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我相信可以,我也愿意接受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们的指正。我将不可避免地从美国的处境进行讨论,但我仍希望它可以作为案例,提供一些广泛适用的原则。
两座城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两座“城市”或两种社会秩序中。首先,我们属于“上帝之城”。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指出,上帝之城“由彼此合一的人构成……因着对三位一体上帝的爱……(并)‘爱人如己’。”[1]基督教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爱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个人利益、家庭、民族和国家不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其次是“人之城”——不是基于爱和舍己,而是基于权力、剥削和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社会秩序。人之城的运作原则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服事他人,而是用他人的生命服事自己。
一、关于人的两个圣经神学真理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还提炼并教导了关于基督徒与政治秩序关系的两个关键原则。[2]但要探讨基督徒如何在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人的本性,在此,有两个方面需要牢记。
首先,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被造的,但堕落了。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极其宝贵,同时在本性上又是自私且邪恶的。这与“塑造大多数历史解释的普遍世俗观点相悖,……世俗观点以人天性善良为基础,将人类误入歧途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经济、政治、心理或宗教等环境因素。”[3]上述观点认为善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恶则来自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实际上,社会系统可以加剧邪恶,但却不能凭空产生邪恶。社会系统之所以变得邪恶,是因为人心邪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是善良的,而社会系统是邪恶的。
其次,我们必须牢记,基督徒并未幸免于人类的堕落。善与恶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这种两面性也存在于宗教人士和基督徒之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基督徒都是善良的,非基督徒都是邪恶的;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世俗总是更好的,而基督徒都是偏执狂。
二、政治原则
如果理解了以上关于人的神学原则,我们就可以明白随之而来的政治原则。例如,我们既要避免左派的乌托邦主义也要避免右派的怀旧悲观主义。基于人的两面性,奥古斯丁“两座城”的观点能让我们免于陷入这两种误区。它保护我们免受左派常见的天真理想主义的影响——即认为过去是可怕和压迫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因为恶不在于人而在于社会系统。按照这种观点,政治成了宗教和救赎的一种形式。它也使我们免于右派的常见缺陷——试图重现的过去不过是另一种人之城的黄金时代,却忘记了上帝之城必将得胜。
同样,我们也要避免左派和右派的简化主义。例如,我们必须牢记,人心是恶的根源。尽管社会系统可能加剧邪恶,但社会或社会结构并非恶的根源。[4]这一观点不同于左派,它们过度信任国家并认为政治力量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还必须牢记,基督徒也是罪人,文化或权力在基督徒手中不一定会更好。这一观点也不同于右派,它们过度信任基督徒掌权或控制文化,并过度依赖自由市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世上的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与上帝之城相提并论。对一些人来说,奥古斯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指出任何人之城或政治实体都不是上帝之城。其神学原因有很多,这里主要讲两点。首先,上帝的国度是“已然-未然”的。因此,直到上帝亲自建立他的国,人类无法创造完全的基督教社会。其次,福音具有文化灵活性。并没有一卷新约的“利未记”来告诉基督徒在具体的文化处境中该如何生活。因此,基督徒有自由和责任在不同的文化中将福音处境化,这超出了与预先建立的政治秩序保持一致的范畴。因此,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上帝之城(通过圣灵部分性地实现)和人之城;既不能混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也不能认为二者是完全分离的。这既反驳了可以有一个主要的基督教政治计划、政党、社会秩序或文化的想法;也反驳了基督徒可以通过不参与政治从而退入属灵领域的想法,因为放弃政治变革实际上就是支持政治现状。基督徒必须让信仰引导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避免陷入偶像崇拜。
因此,当参与文化和政治时,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期待,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完美,事情总是有好也有坏。基督徒首先是上帝之城而非人之城的公民(参腓3:20)。因此,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乡。我们要成为地上城市的邻舍和参与者(参路10:25,耶29:4-7)。地上的所有城市也是好与坏的混合体。但总体而言,它们以人之城的结构和动机为主要特征,但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和基督徒的影响,许多社会也表现出一些上帝之城的平安与公义。同时,我们必须记住,虽然我们希望教会本身是更多地被上帝之城的价值观塑造,但教会也是不完美的善恶混合体。
任何政治运动或政党都存在伟大的美德和与邪恶共谋之间的矛盾。参与政治的基督徒既应该是团队的好成员,也应该是所属政党的批判者,因为带着良好意愿的世俗或非基督教观点都会将某些东西偶像化。例如,左派会过于信任政府,而右派则过于信任市场。结果和方法上的善恶混合也适用于那些追求行善的彻底的基督教组织和运动。正如乔治·马斯登所言:“面对那些与基督教信仰原则对立的文化力量,信仰有时可以调和这种张力,但往往反而被这些力量重新塑造。”[5]
圣经的国家观
一、耶稣的教导与神权政治的国家观
在马可福音12:13-17和路加福音20:20-26中,法利赛人拿着罗马的银钱问耶稣是否应该纳税给凯撒,试图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耶稣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12:17,路20:25)这表明我们不应该期待人类政府完全基督教化,同时“政教分离”的理念确实有其圣经依据。圣经学者卡森(D. A. Carson)说:
“在严谨的神治观念检验下,耶稣的话语有些不一致:神是藉着君王的手掌权,因此神治与人治的范围很难区分。白纸黑字明明写着旧约的架构与神治密不可分。然而,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必须在凯撒与神之间划分清楚。当然,这不是说凯撒的统治权在神的管辖范围之外,也不是说神完全不插手。但是无可讳言的,对立约之民来说,耶稣的这番话却带来了根本上的改变。立约之民已不再是神治的国度(如旧约以色列民),它现在是各地教会的聚合,且在许多‘君王’与‘凯撒’的统治之下,但是却不崇拜其中任何一位。这就是全世界许多基督徒在探讨无统治结构之宗教历史源头时,会追溯到主耶稣这番话的原因。”[6]
同样,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否则,他的仆人会奋战以阻止犹太领袖逮捕他(参约18:36)。耶稣的国属于另一个地方。这正是奥古斯丁所强调的主题:基督徒确实是为一个国度而活——基督的国——但基督徒却不应该认为他们要通过强制性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它,或将上帝之城视为任何特定的地域或政治秩序。夺取国家权力,刀剑的权柄,不是为基督的国度而活的方式。基督的国度“属于另一个地方”,它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因此实现基督国度的方法也不同于这世界的方法。正如舒尔特福(Ernest Shurtleff)在1887年的赞美诗《永恒之君,求引领》(Lead On,O King Eternal)中说:“非藉刀剑的交锋,非藉战鼓催声,乃藉遵行主大爱,天国才能降临。”[7]
二、耶稣的教导与极权政治的国家观
虽然上述针对现今神权政治观念的说明,澄清了基督徒不应尝试夺取权力或试图建立完全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耶稣告诉彼拉多,只有在上帝的许可下,他才能享有世俗权力。耶稣反问银钱上印着的是谁的形像,这强烈地表明,我们的最高忠诚对象必须永远是上帝,因为我们有他的形像。圣经明确表明,如果国家法律要求基督徒违背上帝的律法,基督徒可以抗命。在使徒行传第5章中,当公会审问彼得和众使徒时,他们直接陈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当极权国家入侵家庭和教会的领域,并试图在各个方面指导其生活时,基督徒必须反抗。
三、新约的教导
提摩太前书2:1-2、提多书3:1以及最著名的罗马书13:1-7教导我们,国家(甚至是异教国家罗马)是由上帝设立的,是“神的用人,是有益的”。由此可见,国家有两个基本功能。首先,国家拥有“刀剑”的权柄(参罗13:4)以对抗邪恶,这是国家的强制力。它可以通过罚款、监禁或处决强制其公民遵守法律;也可通过”刀剑”的权柄保卫国家免受入侵。以上情形都表明国家在对抗“邪恶”。其次,国家还应服务于“你的益处”(参罗13:4)。有些人试图争辩说,国家服务于其人民益处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刀剑的权柄惩治邪恶。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不需要为穷人提供教育、食物以及物资。他们认为由国家执行的约瑟的饥荒救济计划(参创41:47-57)是完全错误的。该立场(主要是政治上保守的美国评论员)认为政府应扮演有限的角色,并且主张极低的税收和精简的政府。但是大多数释经家,例如道格拉斯·穆尔(Douglas Moo),则认为罗马书13:3-4教导国家既有促进公共利益的职责也有惩治不法行为的职责。
尽管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许多人希望大力限制国家的角色(或使其成为神权国家),然而,反之也同样存在危险。人们可能视国家为救主,依靠国家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最终,国家可能会全面控制人们的生活、压迫所有反对力量,并限制宗教自由。这也是耶稣教导基督徒必须避免和抵制的。启示录谈及了这种类型的政府。启示录中的统治者崇拜(参启13:15)显然是指敬拜罗马的凯撒,即要求人们向凯撒献祭并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但大多数人认为启示录在这里指向的是历史上所有的极权政府,它们将自己当作神,变得像魔鬼一样,逼迫上帝的子民。
讲道与政治立场
牧师在讲道中面临着一个微妙的任务:在涉及道德问题时,避免在讲道中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场或公共政策。但牧师应该教导圣经中提到的具有政治含义的问题。例如,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如何对待外邦人和移民的教导,然而要知道在当今的文化中实践这些教导是很困难的。在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及其他地方,移民问题是一个紧迫且具有分裂性的政治议题。与之性质相似的贫困和不公正的问题,圣经也有很多相关教导。圣经关于性别与性取向的教导在许多国家也同样被视为政治问题。
面对这一任务,需要承认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 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都不应因为某些问题敏感就避开深入地研究圣经文本和讲道。那是懦弱的表现,是在逃避教导信徒“神的全部计划”(参徒20:27,新译本)的责任。
- 我们也应避免过度解读经文,以支持某些政治政策、党派或候选人。
- 我们还应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指控,即暗中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政策(即使我们在尽力避免造成这样的误解)。
例如,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谈及移民时经常使用贬低性语言。牧师可以宣讲许多圣经的经文,倡导关怀、尊重和关注移民和难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讲道会因为持守圣经的立场和态度造成对某些政治人物含蓄的批评。然而,圣经没有授权牧师具体指出国家的移民政策应该如何。一个国家每年应该允许5万、50万还是100万合法移民?因为圣经并未教导这种细节层面的事务,所以牧师不应试图支持某一具体政策——至少在讲台上不应该,因为讲台所宣讲的代表了整个教会。
群体偶像与相互竞争的政治秩序
奥古斯丁指出,人之城必然基于偶像崇拜。也就是说,任何政治秩序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竭力地以三位一体上帝为根基,都必然会制造偶像。人之城总是制造社会和文化偶像,即将上帝以外的事物置于首位。不仅是整体的文化会制造偶像,具体城市也如此。马克·吐温说:“波士顿人问,他知道多少?纽约人问,他值多少钱?费城人问,他父母是谁?”在这则笑谈里,三座城市的偶像昭然若揭。
奥古斯丁通过分析每一种政治文化的“至爱的普遍之物”[8]为基督徒分析政治和社会秩序提供了批判性的工具。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9]和大卫·科伊齐斯(David T. Koyzis)[10]这两位当代思想家分析了现代西方基本且反复出现的政治驱动力。虽然这些分析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文化,但鉴于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力,这些分析可能具有参考价值。
一、西方的偶像(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强调西方至少主要有四种偶像:
1、浪漫主义,将个体偶像化。最近,这又被称为表现型个人主义[11]——认为最高的善是跟从本心、表达自我,并实现自我最深的梦想和愿望。尼布尔认为,这种“崇拜个人里面的某种独特力量……是自我荣耀的古老宗教”[12]。
2、理性主义,将科学、技术和理性偶像化。浪漫主义视自由的自我表达为一切的答案,理性主义则视科学为救主。“人本理性主义忘记了人类理性……是一种衍生的、依赖的、被创造的现实……它认为随着理性主义的逐步发展,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邪恶终将被消灭。”[13]
3、民族主义,将种族和国家偶像化。尼布尔提到了“血与土”,这是纳粹宣传一个种族(Blut,血统)和土地(Boden,土地)的口号。法西斯主义理想化了农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而城市则充斥着外国人。尼布尔称这是“种族……和国家的自我荣耀”,而非个人的自我荣耀。
4、社会主义,将国家以及受压迫者(“无产阶级”)的视角和行动偶像化。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看到了所有‘聪明人、强者和贵族’的伪装”,但随后他指出“无产阶级的生活与至高者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合”[14]。尼布尔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偏好,认为它优于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请记住,这是写于1937年),但他同时也准确地补充道:“正如所有文化一样,如果没有降服于独一至圣的上帝、造物主、世界的主和审判者,(马克思主义)最终也会陷入自我荣耀的罪。”[15]
二、西方的意识形态(大卫·科伊齐斯)
科伊齐斯观察到西方至少有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
1、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个体的自由主义偶像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追求以个人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社会。他们认为,最佳的社会型态不是由具有共同的宗教或文化价值观联结的社会(如民族主义),而是基于唯一的价值观——只要不伤害他人,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20世纪中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继失败,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甚至分化成了两个彼此竞争的分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两者都属于自由主义,因为它们都假设个人自主(选择)的首要性,并追求建立精英社会。[16]
保守派将市场和企业精神偶像化。他们相信,最佳形式的社会型态是拥有自由市场和由小政府通过监管和税收维护的公开的竞争。他们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境负全部责任——在自由国家中,一个人如果贫穷,那是他自己的错。保守主义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商业世界。自由派将科学、专业知识和自我表达偶像化。他们认为,所有关系都是交易性的,并简化为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达成的契约。他们相信,科学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们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精英文化团体。
2、民族主义,将其人民和国家偶像化。无论是公民国家还是民族国家,都可能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份,偶像崇拜随之渗透。它始于“美化”国家的历史——掩盖过去的不公义。民族主义的偶像总是要求人们对他们的祖国和“人民”献上最高的忠诚。这意味着以多种方式排斥“非我族类”:消灭(驱逐)、统治(允许他们存在,但权利较少,可能会被威胁)、同化(除非放弃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否则会被大多数圈子拒绝)或抛弃(故意忽视他们的基本需求)。
3、社会主义,将种族、性别和性身份偶像化,并期望政府满足其需求。自由主义认为人的处境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则认为罪和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副产品。他们认为自由选择、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不过是当权者保持其权力的诡计。
如今,现代进步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利用性别、种族和性取向来获取权力。这些信念认为,我们的主要身份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群体间的不平等从来都不是内部因素造成的——绝不是个人努力或群体文化的结果。相反,外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系统因素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解决方案不是改善自我或强化家庭生活,而是社会政策和转移权力。唯一的前进之路是通过国家重新分配权力,破除为社会群体积累权力的信念和话语体系。
三、总结
总之,我们看到这些意识形态有以下共同点:
- 将某些美好却堕落的东西偶像化(如国民、自由市场、个人自由、科学理性、种族、性别或政府)。
- 将某些美好但堕落的东西妖魔化(如其他种族和文化、政府和大组织、宗教和家庭等道德权威或自由市场)。
- 倾向于排斥和边缘化被视为敌人的群体,并偶像化被其视为拯救的群体。
- 未能认识到恶的复杂性。圣经告诉我们,世界、肉体和魔鬼是恶的来源。进步主义者只看到了世界——即系统性的恶。保守派只看到了肉体——即个体的道德邪恶。民族主义者对这两者都有一定的认识,但仅限于其他文化。它们都没有意识到魔鬼——从属灵的层面看待世界的邪恶。因此,无论是为社会还是个人,它们只能提供简化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世俗的盼望都将失败,因为不符合世界既美好又堕落的复杂现实。
反思
1、基督徒不能完全支持或认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根据圣经的观点,在处理种族和经济不公正的问题时,这些意识形态有的过于强调系统性、结构性因素,有的则过于轻视。一些过于强调个人责任,而另一些则反之;一些过于个人主义,而另一些则过于集体主义;一些过于不信任市场,并过于信任机构和政府,而另一些则有相反的问题。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但讽刺的是,两者都将群体、种族或阶级身份视为绝对的。一些意识形态过于反宗教,而另一些则倾向于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一些认为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但金钱却不行[17];另一些人则认为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钱,但必须遵守传统的性道德。一些倾向于神化传统家庭并夸大性别差异,而另一些则颠覆传统家庭并试图模糊性别差异。一些相信科学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道德价值,而另一些则非常不信任科学。一些美化穷人,而另一些则妖魔化穷人。一些拒绝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任何改革,而另一些则希望彻底废除它。
2、基督徒既不能不参与政治,也不能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学派或政党持不加批判的态度。不参与政治(在政治上不活跃,甚至不投票)实际是在支持政治现状。罪的教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社会不需要改变,也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公正。因此,基督徒的处境很尴尬,不得不在被一种或多种偶像所支配的党派中投票,尽力维护所支持的计划中的积极方面,同时批判(并且不忽视)其中的错误甚至有害的因素。
3、共同的基督信仰必须成为比共同的文化、种族或政治更强的纽带。如前所述,奥古斯丁指出,所有基督徒都同时生活在人之城和上帝之城中,但我们的首要忠诚和国籍属于上帝之城(参腓3:20)。然而,许多基督徒公开地否认或攻击那些与他们有相同信仰但却有不同政见的基督徒。与信仰相同的人相比,他们与政治立场相同的人更合一。然而保罗坚持基督徒不能让法律上的分歧超越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参林前6:6-7),或模糊他们的主要身份(参弗2:19;来13:14)。当整个教会被视为某一政党的马前卒,而不是一个超越政治的实体时,世人就会认为宗教只是那些攫取权力之人的幌子。
4、依照圣经,基督徒的做法截然不同(就世俗的类别而言)却不一定是中立的。基督徒不应将无党派视为中立主义——即在两极之间寻求折衷的温和立场。当面对世俗思想光谱中的两极选择时,例如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一元论与自然主义、律法主义与反律法主义,基督教都从根本上对每一种选择进行批判,同时不忽视任何源自上帝普遍恩典的见解。它不是在两极之间的光谱上选择,它的立场是在光谱之外。沃特金称之为“圣经的对角化”[18]。在政治方面,基督徒依照圣经的做法不是中立的而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徒在性伦理和贫困问题上通常持有非常坚定的立场,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这些立场可能显得很极端。因此,在和非基督徒一起工作的时候,基督徒经常会发现自己在某个问题上与之一致,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却与之相左。
基督徒参与政治的实际措施
1、在政治光谱上多方面积极参与。 圣经通常(并非总是)为我们提供道德和规范,而非详细计划,说明如何在民主、多元化的社会中推行这些规范。例如,我们应该致力于帮助穷人和移民,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税收应该有多高或多低,应该建立什么结构来支持穷人,等等。这些是智慧和审慎的问题,而不是顺服圣经具体教导的范畴。这意味着:
- 我们应该友善地对待在政治上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基督徒:在圣经没有明确涉及的问题上,基督徒必须允许彼此就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法上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经典的表述,我们不应在圣经给予自由的地方束缚基督徒的良心。[19])在圣经的绝对原则之内,我们有自由去决定如何做这类事情。在此,我们应该尊重彼此在做法上的不同。
- 看到处于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上的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拥有相同信仰和委身的基督徒,在达成相同社会目标的最佳、最谨慎的方式上可能存在不同的结论。基督徒可能会聚焦于一个或两个问题,因此愿意与在其他问题上观点和做法截然不同的人合作。例如,专注于改革刑事司法系统的基督徒可能会和在其他事情上(如堕胎或性表达问题等)与之意见相左的群体达成共识。另外一些积极参与反堕胎的基督徒,可能会因为良心的缘故而不与那些群体合作,但可能会发现能和在移民或贫困问题上与之观点不同的群体合作。我们应该加入那些整体上符合自己基于圣经的认信的组织和政党。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不应对政治承诺中源自基督教启示的内容保持沉默(或过于大声),也不应对该党派中必然会出现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简化因素保持沉默(或过于大声)。
2、认识到作为组织的教会和分散在社会中的教会之间的区别。 一般来说,教会组织——无论是整个宗派还是地方教会——最好不要为特定的政治候选人和政策募款或宣传。在实践层面上,教会领袖通常不具备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公开声明的专业知识,也不具备管理房产、社区发展公司[20]、学校或其他类似项目的专业知识。我曾看到教会试图在组织层面上“行公义”,却被消耗,从而忽视了教会的本质——通过上帝的圣道和圣礼传福音和训练门徒。另一个问题是党派主义。地方教会不断地、直接地发表政治声明,在不经意之间可能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就不欢迎你来这里听福音。”
然而,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中的教会可能无法奢侈地完全不参与政治。例如,在美国实施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即1876-1965年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以及私刑频发的年代,黑人教会是否应该不参与政治、不批评市政领导的不公正行为?在社会危机时期——例如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教会必须作为组织采取政治立场。当然,在何谓越过“社会危机”这一界线上总是争议不断。
一般而言,基督徒个体应该做光、做盐并参与政治——无论是在现有的政治组织和政党中,还是组建新的志愿协会——以追求社会公平和繁荣。教会领袖不应该告诉其成员要如何投票。聚集的教会是为了传福音和训练门徒,使其作为基督的门徒在世界中工作;分散的教会是基督徒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践行圣经的教导和世界观。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二者的区别。
3、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基督徒都应该定期的、跨越政治派别的聚集在一起。 基督徒必须这样做,以达成两个目的。一是建立关系。我们必须建立并维护友谊,避免陷入对不同政治立场的刻板印象。二是努力达成共识。尽管前面提到圣经没有为我们提供政治蓝图,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反思政治问题时,很少有基督徒会一同深思熟虑地阅读圣经。基督徒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能促使最初在政治立场上相距甚远的基督徒(因为不同的政党和框架有很大差异)因圣经中有关正义、道德和人类繁荣的观点在当前处境中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推荐阅读
1、Johnson, Kristen Deede. “Public Theology.” In Allen, Michael, ed. The New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31–248.
2、Kaemingk, Matthew, ed. Reformed Public Theology: A Global Vision for Life in the World. Baker Academic, 2021.
3、O’Donovan, Oliver.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 Rediscovering the Roots of Political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Smith, James K. A. Awaiting the King: Reforming Public Theology. Cultural Liturgies Vol. 3. Baker Academic, 2017.
注:
[1] George Mars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Brief Histo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8), 7–8.
译者注:马斯登的中译著作,可参考:乔治·M.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之魂》, 徐弢、程悦、张离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同上。
[3] 同上。
[4] 译者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马克思(Karl Marx)认为社会或社会结构是恶的根源。卢梭认为,社会的形成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并带来了不平等和腐化,详见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形成的,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阶级压迫,详见其著作《资本论》,朱登译,武汉出版社,2012。虽然二者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案不同,但是都同样认为社会或社会结构是人类痛苦和不平等的根源。
[5] George Mars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Brief Histo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8), 9.
[6] 卡森 (D. A. Carson),《为了神的爱》,顾华德译,天恩出版社,2006,60。
[7] 胡问宪译,“ For not with swords’ loud clash- ing, or roll of stirring drums—with deeds of love and mercy the heavenly kingdom comes.”
[8] 译者注: common objects of highest love,主要强调将普遍之物赋予了至高的爱,从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方向。
[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a Secular Age” in Robert McAfee Brown, The Essential Reinhold Niebuhr: Selected Essays and Addresses (New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9–92. (译者注: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思想可参考《雷茵霍·尼布尔》,王崇尧著, 永望文化事业出版社,1993。)
[10] David T. Koyzis, Political Visions and Illusion: A Survey of and Christian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Ideologies, 2nd edition (Downers Grove, IL: IVP, 2019).
[11]译者注:参特雷文·瓦克斯 (Trevin Wax)表现型个人主义专题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s/expressive-individualism
[12] Niebuhr,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a Secular Age,” 80.
[13] 同上,81。
[14] 同上,82。
[15] 同上,83。
[16] 参Patrick J. Deneen, Why Liberalism Failed (New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 译者注:美国自由主义的金钱观主张政府干预财富分配,而保守主义则坚持财务自由。
[18]参Christopher Watkin, Thinking Through Creation: Genesis 1 and 2 as Tools of Cultural Critiqu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7), 26–28。详见本书第六章“圣经高阶理论”。
[19] 参《威斯敏斯特信条》20章第2条。
[20]译者注: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简称CDCs,是非营利组织,通过提供项目、服务及其他方式促进和支持社区发展。CDCs通常服务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例如某个社区或城镇,尤其关注低收入居民或面临困境的群体。其活动范围较广,包括经济发展、教育、社区组织以及房地产开发等。这类组织通常与可负担住房的开发密切相关,通过相关举措来支持并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development_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