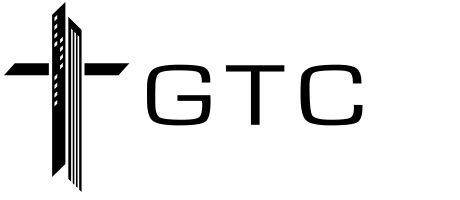“福音改变一切”,这是城市植堂运动(City to City)最常说的一句话。这意味着,福音不仅关乎个人得救,也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福音是基督徒成长的每个阶段的推动力,以及应对一切困难和挑战的资源。福音带给我们新的动机,重整我们内心爱的秩序(包括我们所有的关系),重塑我们的行为,更新我们使我们像基督。唯独福音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称这个过程为“个人的福音更新”。
什么是个人的福音更新?
福音明确呼召基督徒听到福音信息后,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要在恩典中成长(参彼前2:2-3;3:18),在属灵里成熟(参来6:1),在仁爱、节制、坚忍、和平、喜乐、谦卑、恩慈、温柔、良善、信实和忍耐中成长(参彼后1:5-8;加5:22-25)。藉此,我们将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参弗4:13-16)。正如以弗所书4:24教导我们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上述经文有力地告诉我们,深刻的生命更新是基督徒生命的标志。因此,每一间教会和每一项基督徒事工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实现这种改变。
什么才能带来这种生命的改变呢?答案是:上帝的话和圣灵。新约圣经在教导基督徒成长的时候,会谈到圣道和圣灵的关系。以弗所书5:18-21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满有喜乐、感恩,出于对基督的敬畏而彼此顺服。歌罗西书3:16-17告诉我们:当把“基督的道理”(释经家认为是福音,即救恩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1],使我们用诗歌彼此教导,赞美上帝,凡事谢恩,彼此顺服。
换句话说,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经历的两个方面:“被圣灵充满”和“丰丰富富地领悟福音”以经历生命的更新。正是圣灵使上帝的话语在人心中如此清晰和真实,也使我们里面充满喜乐的颂赞,并改变我们所有的关系。此外,圣灵透过福音作工,圣灵不是以某种神奇而抽象的方式把力量注入到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是向我们彰显基督和他的救赎,使我们的心以之为荣耀和美善(参约16:14)。圣灵通过福音作工,福音通过圣灵成为赐生命的大能(参罗1:16-17)。圣灵的更新就是福音的更新,反之亦然。
上帝的恩典是个人生命改变的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更新力量,整本圣经都见证了这一原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上帝并没有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说:“你们遵行,我就拯救你们。”相反,因着恩典,上帝拯救了他们,然后赐给他们律法,意思是说:“因为我救了你们,所以你们要遵守律法。”诗篇105篇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原则:上帝救赎的恩典会带来更新、圣洁的生活。诗人列举了一长串上帝的拯救作为,包括赐给以色列人土地,这土地既不是他们赢得的,也不是他们劳碌得来的(参44节),接着说到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45节)换句话说,生命的改变是恩典(或者说是,正确地领受恩典)的结果。
对福音的信心和对福音的深刻理解是个人生命改变的动力,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保罗的祷告中。保罗的祷告内容非常丰富,但所有祷告的核心都是祈求读者能“真知道”上帝(参弗1:17-18)。怎样才能真知道呢?只有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心中的眼睛才会被“照明”,从而知道我们接受基督后所得到的基业是何等丰盛。保罗在祷告中祈求,通过圣灵我们能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3:18-19)。基督徒相信,上帝如此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参约3:16)。但保罗说,只有越来越多地“抓住”和“知道”这些福音真理,我们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参弗4:13)。
在保罗关于改变的教导中,哥林多后书3:17-18是最具启发性的经文之一。保罗说,藉着圣灵,我们因信“看见”耶稣的荣光,使我们逐渐“变成主的形状”。约翰·欧文(John Owen)在《基督的荣耀》一书中说到,只有透过基督的福音,我们才能看到基督的荣耀和荣美。欧文详尽地说明,看见基督的荣耀不是抽象地了解有关基督的知识,而是渴慕默想他的属性、位格和工作——因着基督的所是和他的作为使我们得了自由——基督的荣光照亮我们的心,并由内而外地改变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人性的荣美时,我们就会明白,他取了人的样式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我们看到耶稣将自己献上为祭,为拯救我们付上何等代价时,我们才能充分体会到他爱的荣美。
福音如何更新个人的生命
福音是我们追求圣洁和敬虔生命更新的全新动力与热情,是一种内在的火热。从前我们追求圣洁的动机是自我中心的,很可能是为了得到祝福和进天堂。然而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追求圣洁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与使我们犯罪的动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律法主义的宗教人士的生活会从恪守律法变为随心所欲。事实上,他们遵守律法一直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上帝。对他们而言,顺服上帝是一种责任,而不是喜乐,也不是出于内在的喜悦;虽然有时他们会感到满足,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满足。然而,当我们抓住并经历了上帝恩典的福音,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一切祝福(为此,耶稣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就有了顺服上帝的全新动机。我们想爱上帝,就像他爱我们一样(参约一4:19)。如今,我们顺服上帝是为了更多地得到上帝:更像他、更讨他喜悦、更认识他。如今,我们以上帝的幸福为我们的幸福,在他里面寻求我们的喜乐。如今,我们只因上帝荣美的所是而爱他。这才是真正的爱。福音帮助我们真正地爱上帝,从责任变为选择。[2]
福音使我们得到全新的自由,使我们摆脱驱动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深蒂固的罪。马丁·路德说,在你违反第二到第十条诫命以前,你已经违反了第一条诫命。例如,除非我们把赚钱看得比顺服上帝更重要,否则我们不会为了赚钱而撒谎。换句话说,所有的罪都源于我们“心中的偶像”(加尔文),或“失序的爱”(奥古斯丁),或“错误的身份认同”(克尔凯郭尔)。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制造了偶像;而偶像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在受造物中而非在耶稣里面寻找称义、自我价值、成就感、安全感、意义和目的。偶像不仅是假神,更是假福音:“如果我拥有这个,我就会被称义、被爱、被接纳。”
无论我们把救赎和自我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它都将成为我们必须拥有的东西——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于是,那些承载了自我救赎以及自我的事物就会奴役我们,成为我们行为的驱动力。然而,耶稣的爱和公义是礼物——只能接受,不能靠自我成就来实现。唯有接受耶稣赐下的礼物,才能带给灵魂真正的安息。
虽然从原则上讲,基督徒不再依靠这些偶像来称义和获得幸福,但在实践中却常常不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基督徒心中的偶像仍然紧紧抓住他们不放。要想从上瘾、虚假的爱中得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心思意念更深地放在耶稣身上,并且在践行福音的信心中不断成长。不再继续认为“因为我成功、美丽或有道德,所以我是好的”,而是思念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参西3:1-3)。正如托马斯·查莫斯(Thomas Chalmers)所说:“使(心灵)摆脱旧情感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新的情感来取代。”[3] 这是在福音的自由中成圣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思念”基督和上面的事,另一方面是 “治死”我们里面的罪(参西 3:1-17)。
福音不仅重新定位了人心之所爱,还为我们反思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行为和实践提供了思考框架。世人是在道德主义的律法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反律法主义的光谱之中思考道德问题。一端是严格的、规则导向的行为主义——认为我们要做到某些行为才能成为好人。另一端是无规则的情感主义——认为我们要创造和活出自己的真理,通过表达自己的欲望来成为好人。福音却不在这个光谱之上;福音“对角化”(diagonalizes)了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这两种选择——福音不仅批判这两种选择,还在既没有混合也没有借用它们的基础上,满足了这两种选择背后的渴望。[4]我们唯独靠信心得救,而不是靠遵守律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得救必然导致一种遵行律法的新样式,其基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责任,而是被爱充满的喜乐。
福音的光谱——既不是道德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成为生活导航的新框架。福音避免自由主义(倾向于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于道德主义),同时也不是把我们带到中间地带。福音的框架使我们有独特的行为和实践。请看加拉太书第2章中保罗对彼得的责备,那时彼得又陷入了种族骄傲和特权的道德主义之中。保罗并不只是说:“彼得,你需要对其他种族和民族更加开放。”相反,他责备彼得“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加2:14)。保罗认为,因信心和恩典得救的信仰对我们看待其他种族的方式有重大影响。福音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并提供新的原则(参加2:11-16)。
下图展示了新的内在的火热、新的自由和新的框架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福音更新。
称义和成圣的关系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藉着基督得救的福音,不能简化为“因信称义”的教义。长期以来,一些人坚持认为靠着白白的恩典得救是生命改变的阻碍,因此新教的改革宗教义一直是他们的攻击目标。然而他们低估了基督徒改变的逻辑和动机。他们认为,如果无需品格的改变就已经得救且被上帝完全接纳,那么我们就没有动力过圣洁的生活。一位自由派神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写道:“那些后来把(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作为基督教信仰中心的人都悲惨地发现,从逻辑上讲,在这种救赎概念之下,无法从中得出任何道德规范。”[5]史怀哲和其他的批评者们陷入了严重的谬误。成圣(改变)不是与称义无关的,也不是与称义割裂的,称义是成圣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具体阐述这一点。
称义使我们确信上帝的爱,并通过感恩的喜乐带给我们新动力。唯独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领受了救恩,人追求圣洁的动机才会从利己(讽刺的是,利己却是与敬虔对立的)转变为在爱中的服事。《比利时信条》第24条说:“‘使人称义的信心会让人疏忽敬虔与圣洁的生活’这一观点是大错特错的。相反,没有这种信心,他们就绝不会出于对上帝的爱而作任何事,只是出于自爱或惧怕刑罚。”[6]
这意味着,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因着基督已经完全地、白白地领受了救恩,我们才会出于对上帝的爱而行善。在我们真知道福音之前,我们的善行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在自己的正直中获得安全感,让上帝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的道德行为是为了自我救赎,是出于恐惧和骄傲,因为我们没有在福音里将身份建立在基督身上。如果我们寻求的是通过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么当我们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时,就既不是为了她也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若我们的动机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善行就无法成为敬虔和圣洁的。按照这种逻辑,没有称义,成圣就不可能开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善行根本不是善的,并且选择单单信靠基督时,我们的善行才会开始成为善的(这一点很吊诡)。如果没有深深地抓住恩典,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沦落为积功德——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是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以及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好行为就越是出于为他而行——爱他、效法他、服事他、取悦他。只为耶稣!
只有以喜悦、欢欣和感恩的心回应基督那宝贵的恩典时,基督徒的归顺(submission)、顺服(obedience)和降服(surrender)才是健康的,才是真基督徒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深,我们的救主为拯救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浩大,由此,我们对他的顺服才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不再是自私的顺从规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再是有条件的顺服(只为得到我们以为应得的祝福)、也不再是无喜乐的遵守规则(不是出于喜爱,也不能持久)。相反,真正的顺服,源于我们已经拥有上帝的爱、永生并且永远与上帝共同治理万物。
因此,顺服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好像还有比永生更伟大的的祝福似的)。我们顺服只是为了爱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主,效法他,得他的喜悦。我们的顺服不是有条件的,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的环境,乃是与上帝的丰盛息息相关。我们的顺服不会毫无喜乐,不会为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哀叹,更不会因事情不合心意而抱怨。顺服之所以是喜乐的,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与耶稣为爱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我们因顺服所付出的代价根本算不得什么——哪怕这意味着要为我们的信仰献上生命。因基督已经付上的赎价,我们因顺服和作门徒所要负的 “轭”和“担子”都是轻省的(参太11:30)。
总之,倘若如史怀哲等人所言,“纯粹因恩典而得救在逻辑上和情感上挪去了过圣洁生活的动机”,那么被恩典所挪去的主要动机就是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惩罚和定罪的恐惧,就失去了道德生活的所有动力,那么这就表明我们最初顺服的唯一动力是恐惧。出于恐惧的行为是自我为中心的,是与爱相悖的——真正的爱是舍己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一 4:18)
称义和偶像
称义带给我们与受造物全新的关系,并重整了我们内心爱的秩序,使我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每个人都是为某些事物而活,都会寻找某种东西来承载生命的主要目的、意义和安全感。如果那不是上帝,那么它必然会成为偶像、占据我们心中的首位,成为虚假的救主。如果我们觉得离开某个事物就活不下去了,那么它就成了我们的主。然而,出于上帝无价的恩典,他拯救我们,使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从而改变了我们与受造界的关系。上帝所造的万物成为美好的礼物,而不再是偶像或对偶像的威胁。
从因信称义的视角看世界,我们周围的一切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造物主——律法的制定者如今是我们的天父。不仅如此,邻舍也不再是我们舒适、安全、幸福的威胁(或最终的来源),而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礼物。马丁·路德赞叹道:“这种对上帝恩典的信心和知识,使人在与上帝和(他所造的)万物相交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勇敢和幸福。”[7]
对称义的认识打破了偶像对我们的辖制。如今,万物(通常)是我们可以之为欣喜的美好事物,却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以及追求成功的过程中,那些拦阻我们的人和环境再也无法夺走我们最终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意义感。因为这些都在基督里,且永远不会失去。
生活中的新身份
称义赋予我们全新的、舍己的、向外关注的生活态度。称义的教义使我们不再自我中心,这表现“在每一个层面上:与上帝的关系(不再倚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不再专注于自己的义)……宣告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将罪人从自我里呼召出来,在信心中倚靠基督,爱我们的邻舍”。[8]
在《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一书中,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追溯了现代身份认同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这一概念,即完全向内的、自我肯定的身份认同。在这种身份认同的模式中,个人内在的欲望和追求被视为比任何外在于自我的东西都更真实。然而,称义的教义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它不是向内发展的,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既释放了我们,也把我们从自我中拯救出来。我们不是在自我之内寻找救赎,而是在自我之外得到救恩之道。称义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服事上帝和邻舍不再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而是从已经被爱充满的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耶稣告诉我们:“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参太10:39,16:25)。称义造就了舍己的人,而世俗文化的“缓冲自我”只能塑造追求自我实现的人。
理查德·拉弗雷斯(Richard Lovelace)在《属灵生命的动力》一书中写道:
“在目前自称基督徒的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坚定地支取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称义之工。[9]……我们把很多问题归结为教会成员在成圣方面有缺陷,实际上是他们在称义方面迷失了方向。有些基督徒不再确信,上帝不看他们现在的属灵成就,只是在耶稣里爱他们、接纳他们,他们是潜意识里根本没有安全感的人——比非基督徒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很多真理的光照,在基督教圈子里不断接受关于上帝的圣洁和自己应有的公义的信息,因此无法安息。他们的不安全感表现为骄傲: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义辩护,以批评他人来自我防卫。他们自然而然地憎恨其他文化风格和其他种族,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释放自己强忍的愤怒。他们拼命坚持律法式、法利赛式的义,但是嫉妒、猜忌和罪恶之树的其他枝条都从他们不安全感的罪根中生发出来。[10]……(相反,在福音里),在每一天开始时要完全与路德站在一起:你已经被接纳了,要凭信心向外看,把基督那完全外源性的义作为自己被接纳的唯一理由,在这样的信心中放松自己,它能使你渐渐成圣,因为信心必然带来活泼的爱和感恩。[11]”
双重过程
福音驱动的内在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双重过程。以弗所书第4章和歌罗西书第3章中(另见罗马书第8章)用了不同的方式描述这个双重过程。清楚起见,我把它们分别称为“治死罪”和“改变心”。
首先,什么是“治死罪”?在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中,被治死的是“epithumia”,即无度的、奴役人的欲望(以弗所书4:22译为“私欲的迷惑”;歌罗西书3:5译为“恶欲”)。歌罗西书3:2说,我们思念的都是地上的事。我们在其上栖息,建立我们的生命,并以之代替上帝,在其中寻找我们的身份、意义、救赎和爱。偶像就是那些被我们视为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为了得到心里想要的,我们会过度工作、说谎,甚至欺压、伤害、虐待他人或自己。“治死罪”就是竭力除去生命中的偶像,让我们的心远离它们,减轻或除去偶像对我们的控制。
其次,“改变心”意味着什么?正如17世纪英国神学家约翰·欧文所说的“因信看见基督的荣耀”(林后3:18),改变心是指让心思和意念定睛在“上面的事”,就是耶稣(参西3:1-3)。藉着道和福音,基督已经显明出来,唯有当我们的心被基督的爱激励时,才能真正打破偶像的枷锁得自由。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使用恰当的经文来默想基督,让基督取代我们心中的偶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渴望从偶像中得到的是爱、价值、安全感、荣誉,还是其他的事物,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要不断默想耶稣的荣耀和他的作为,直到他开始吸引我们的心归向他。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不会被其他事物束缚。我们的目标是让耶稣基督取代我们内心深处的偶像,唯有基督才能真正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
“治死罪”和“改变心”是彼此连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看到更伟大、更吸引人、更美的对象——耶稣,我们就无法除去内心对权力、认可、舒适和控制的过度的欲望。唯有看到了耶稣,罪才会失去吸引力,我们才能得到自由。另一方面,若没有在基督里被接纳的确信和知识,那么承认我们的罪则意味着极大的痛苦。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做好人上,而不是建立在基督身上,我们就无法承认自己的缺点和罪。然而,我们越认识基督的爱,就越容易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越多地认罪,就越能经历到耶稣的恩典是何等宝贵和奇妙。
实践中的福音框架
福音不只是改变人的内心。福音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即我们当如何行事。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案例来探讨这一原则,并比较道德主义、相对主义和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的不同思考框架。
案例1:文化
道德主义者倾向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他们很容易陷入文化帝国主义(也称“民族中心主义”),试图为自己的文化附加属灵意义,以让自己在道德上有优越感。这是因为道德主义者缺乏安全感——面对永恒的律法,他们内深知自己无法遵守。他们把文化差异转化为美德,以强化自以为义的感受。
相对主义者表现出来的不是文化的帝国主义,而是文化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因此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美,每种文化都应该被接纳。然而,这就不可能区分特定文化中的恶与善。讽刺的是,许多对文化持相对主义态度的西方人,却看不起那些不持相对主义态度的传统文化。这样看来,即使是相对主义者,也倾向于民族中心主义(这进一步证明,道德主义和相对主义尽管表现明显不同,但都属于自我救赎)。
然而,福音对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福音使我们对所有文化都持批判态度,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因此,面对上帝的律法,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化能站立得住)。然而,基督徒知道自己完全是因恩典得救的罪人,所以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毕竟,我们得救是单凭恩典,因此我们承认非基督徒的邻舍或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有可能比我们更有智慧或道德。总而言之,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徒对待文化的态度,与道德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截然不同。[12]
案例 2: 苦难
苦难袭来时,道德主义者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道德主义者认为,上帝欠他们的——上帝应该因他们的善行让自己的一生平安无虞。因此,当苦难临到时,道德主义者的内心要么对上帝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达到了道德标准),要么对自己极其愤怒(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道德标准)。他们要么恨上帝,要么恨自己,或者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摇摆。而相对主义者则更容易对生活或上帝产生苦毒,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遇到麻烦。
然而,福音对苦难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福音使我们谦卑,而不是埋怨上帝。一方面,最完美的人耶稣却受了最可怕的苦难,这打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好人就应该过好生活,坏人就该活得差。如果上帝因为爱而甘愿受苦,那么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免受苦难。另一方面,以福音为中心的人不会陷入罪咎感或者自责中。“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罗5:8),就为我们受苦、受死。此刻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可能是为了唤醒我们(参来12:4-11),但不可能是我们的罪应得的惩罚,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接受了刑罚。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已被接纳(也只有这样)时,苦难才会使我们谦卑和刚强,而不是使我们苦毒和软弱。有人曾说,耶稣受苦并非为了让我们免于苦难,而是要在我们经历苦难时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他。
案例3:绝望和沮丧
面对抑郁的人,道德主义者会说:“你违背了律法,应该悔改。”
相对主义者说:“你要爱自己,接纳自己。”
但是,福音引导抑郁者省察自己(我们假设他不是生理性抑郁):“在我的生命中,某些东西已经变得比上帝更重要了,我心里有一个虚假的救主。”福音引领我们悔改,但这种悔改不是仅停留在意志层面上的表面行为。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只能触及问题的表面,无法触及内心深处。道德主义者会强调行为,而相对主义者则强调情感。
然而,福音让我们看到,基督已经更新和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内心、关系、教会还是社群。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偏离了福音,教会中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未能深入地理解福音,未能彻底明白和信靠福音,未能完全照着福音行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福音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想和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城市植堂运动相信,如果充分地宣讲和应用福音,任何一间教会都必将焕然一新。在这样的教会中,人们既能看见对道德信念的持守,也能感受到同情心和灵活性。
展望教会的福音更新
下一章的主题是“教会的福音更新”,那么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或事工意味着什么?有些主张“福音不仅是得救的途径,也是在圣灵中成长和更新的途径”的人,有时会称自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然而,问题在于,在使用“以福音为中心”这个词的时候,可能会显得傲慢——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摆正位置的话,那么可能就真是傲慢的!每个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机构都宣称自己是以福音为基础的,因此,坚持我们的DNA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听起来似乎是在暗示别人没有持守福音一样。所以在使用“以福音为中心”这个词组时,我们会格外慎重。
因此,在使用“以福音为中心”之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清楚地界定。使用这个词标志着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运动,在基督教的核心真理——福音——中合一,而非在次要问题上争论。复兴运动历来都是以新的方式再次清晰地恢复和宣扬福音。宗教改革运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觉醒运动以及许多重要的教会更新运动,都是这样定位自己的。
在事工中以福音为中心意味着什么?根据本文(和下一章)中所探讨的内容,以福音为中心意味着:
- 以福音为中心,不是律法主义。即使正式确认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一个教会或事工的文化也可能是律法主义的。
- 以福音为中心,不是反律法主义。如果不强调效法基督的必要性,或者因惧怕世人的批评,就不能清楚且坦率地宣讲全备的真理,那么这个教会或事工的文化可能是持相对主义的态度。
- 以福音为中心,不是必胜主义(Triumphalist)。如果在犯错时不愿承认自己的软弱,并诚实地悔改,那么这个教会或事工的文化可能存在必胜主义的态度,以至于不得不在不断的改革和重新评估的泥潭中反复打滚。
- 以福音为中心,不是行为主义。如果是以苛刻、专制的方式对人的意志直接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教会或事工的文化可能是行为主义的。如果知道福音重整了我们内心爱的秩序,那么教会则会强调心的问题,并有说服力地鼓励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归正。
- 以福音为中心,不是分离主义。如果因偏离福音而成为律法主义和必胜主义,那么这个教会和事工的文化就可能是分离主义的。这很可能导致教会成为宗派主义,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其他宗派或传统更优越,只有自己才是有智慧的。而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则更愿意与他人合作。
参考资料
1、理查德·拉弗雷斯(Richard Lovelace)所著《属灵生命的动力:福音派更新神学》,(郭春雨译,橡树文字工作室,2020)是一本很好的关于福音更新运动的著作。
2、关于文中所讲的“治死罪”的内容出自约翰·欧文的经典文章《论治死信徒身上的罪》。中译本收录于《胜过罪与试探》,赵刚译,橡树文字工作室,2021。
3、关于文中所讲的“改变心”的内容出自约翰·欧文的经典书籍《属灵之思》,安蒨译,橡树文字工作室,2021;以及《基督的荣耀》,蒋黄心湄译,改革宗出版社,2013。
推荐阅读
1、Brown, Steve. When Being Good Isn’t Good Enough. Lucid Books, 2014.
2、De Silva, David. Sacramental Life: Spiritual Formation Through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VP,2008.
3、Miller, Paul. Love Walked Among Us: Learning to Love Like Jesus. The Navigators, 2014.
4、Rivera, Eric. Unexpected Jesus: How the Resurrected Christ Finds Us, Meets Us, Heals Us. Lexham Press, 2022.
5、Villodas, Rich. The Deeply Formed Life: Five Transformative Values to Root Us in the Way of Jesus.WaterBrook, 2020.
6、提姆·连恩(Timothy S. Lane)、 保罗·区普(Paul David Tripp),《人如何改变》,黄玉卿 、张燕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
7、保罗‧区普(Paul David Tripp),《危机四伏的呼召:教牧事奉独特而艰巨的挑战》,吴苏心美译,美国基督使者协会,2013。
[1]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在英文里用的是“dwell among you richly”(直译为“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种类比,让我们形象地理解被某物充满的画面。
[2] 参加拉太书5:6:“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3] Thomas Chalmers, The Ex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Whearton,IL:Crossway,2020),6.
[4]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五章“世界观和要理问答”。
[5] Michael Horton, Justification, vol. 1, New Studies in Dogmatic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8), 353.
[6] 布莱斯,《比利时信条》,王志勇译,香港雅和博圣约书院·美国雅和博传道会,2013,25。
[7] Michael Horton, Justification,367.
[8] Michael Horton, Justification,373-74.
[9] 理查德·拉弗雷斯(Richard Lovelace),《属灵生命的动力:福音派更新神学》,郭春雨译,橡树文字工作室,2024,第四章之“称义”。
[10] 同上,第六章之“个人更新”。
[11] 同上,第四章之“称义”。
[12] 读者并不难将这一观点应用在当下美国政治两极化的案例上。右派在政治上倾向于道德主义,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传统的(白人主导的)欧洲中心文化;而左派虽然表面上强调多元化和文化相对主义,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主义。他们所倡导的进步世界主义立场往往是轻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