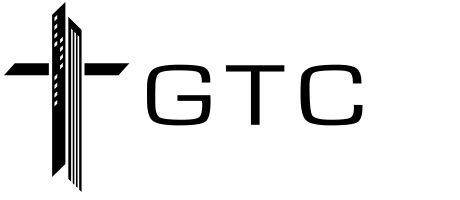作者 侯士庭
我曾经几次到访新加坡,每次都感到这个独特的城邦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日内瓦十分相似。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受训成为一名律师,是担任行政首长的理想人选。同样地,你们当中有基督徒商界领袖,可以在全球化世界贸易中如明灯照耀,以果敢的基督徒领导方式去指引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迈向未来。你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必须在个人和机构层面上彼此联结。然而,我们在服事我们的救赎主、创造主的时候,却常常会因着自身的利益和罪而变得视野狭隘。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儿童故事系列《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共有七册,最后一册名为《最后的战役/The Last Battle》。在这个与基督教文化传承背道而驰的世俗时代,亚斯蓝已死的谣言正在散布,今天许多人相信或愿意相信上帝已经死了,正如尼采(Nietzsche)预言上帝可能已经被杀。C. S. 路易斯在《最后的战役》的第15章中写道,有一个士兵伪装成商人,他遇见亚斯蓝,亚斯蓝对他作出承诺,说:
“光荣的狮王答道:亲爱的,除非你的愿望是要找我,否则你是不会寻找得那么真心实意、那么长久的。因为所有人都能找到他们真心寻找的东西。于是他把气息呼在我身上,去掉了我四肢的颤抖,使我站稳脚步。在此之后,他说的就不多了,只说我们会再相见的,我必须朝更高更深之处去。接着,他在一阵金黄的风暴中转了个向,突然跑掉了。
国王和女士们啊,从此以后,我一直在东奔西跑寻找他,我的幸福是那么了不得,甚至像伤痛似的使我的身体软弱无力。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他竟称我为‘亲爱的’,而我呢,不过是像一条狗。”[1]
基督徒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须“朝更高更深之处去”,而且要更迫切、更超卓。没有什么比上帝的工作更伟大,然而,也没有什么比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和工作——更迫在眉睫。这个来自《纳尼亚传奇》的回响,也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和和我们每天生活背后的回响。
让我们来反思我们所面对的七个原则,从商的弟兄姊妹尤其值得留意。
一、金钱一直都是一种道德真空。
显然,金钱是非道德的惰性物质,如金属——金或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是德国籍犹太人,他后来成为了基督徒,反思了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去“赚钱”的问题。当时正值“工业革命”的辉煌时代。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07)并不是讲述在经济中盛行的机制,而是思考在文化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内在意义如何凝聚在金钱这个交易媒介中。金钱是从互动中产生出来的。然而,齐美尔作出了更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一件东西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呢?第二,人们为何会忘记,金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价值,而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任何价值的呢?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被赋予的价值。当社会不再实行原始的以物易物制度,而是变得日益复杂,并且建立起各种交易机制——如股票交易——后,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果一个名人所拥有的物品被人拿去拍卖,其社会关联会使买家愿意以更高的价钱去得到那物品,因为现在那件物品变得更有“价值”了!每个人都透过与某些人交往,以及疏离某些自己不想跟他交往或扯上关系的人,去塑造自己的社交实体。在这个赋予社会价值的过程中,金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简而言之,“金钱是表达和建立人际关系和互相依赖的一种手段,人总要互相依赖才可以满足个人的愿望”。[2]
在西方世界,人们透过向雇员或提供服务者支付契约性的报酬去制造社会距离,齐美尔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疏离感的力量。因此,他断定,金钱是世俗社会中塑造个人社交实体的最强大力量。金钱成为了表达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好是坏,互相依赖是社会关系中最普遍的形式。推动全球贸易的,是人的情感,而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控制一切的理性。[3]每个股票经纪人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二、金钱与存在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
我需要金钱来换取日用的饮食,从而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更深切地需要金钱去满足情感上的需要,如社会和道德意义等自我追求,或克服基本恐惧。我们的信用卡、购物商场和消费主义,都建立在“空虚的自我”这个迷思上的,并藉此提倡自我满足的观念。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广告业已日趋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强化着人们的自恋心态[4]。现在,科技革命进一步使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深化,其影响更持久,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同工纪克之(Craig Gay)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Downsized: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Diminishment of the Human》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祁克果(1819-1855)曾见证了他的祖国丹麦的改变——从一个僵化、阶级主义、君主专制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的群众社会,以无法识别的市场力量产生出一群“平民”。然而,君王所统治的哥本哈根市,与农民聚居的荒野日德兰半岛,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祁克果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好像荒野上孤独的杉树。杨特定律(The law of Jante)是那里的规范:“你不应与别人不同”,这“一个”观念取代了十诫。1848年的民主革命从政治上把市场力量释放出来,却令这位“存在主义之父”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在他里面有一个“分裂的自我”在不停地问自己:“我是谁?”祁克果明白到,只有走向个人化,变得更自我,像陌生人般与社会保持距离,才是改变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唯一方法[5]。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真正的商业品牌总是这样的。每个企业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存在?”企业领袖更加意识到存在的迫切性,远超于其他行业的人,因为这会对大众带来实时的影响。地方教会既没有这种视角,也没有任何迫切性的需要,去问这个基本的问题,但企业每天都要问这个问题。
三、然而,我们是生存在社会里的人,我们表达群体意识,也需要群体。我可以说这就是企业世界中“为他者的自我”。
我们被造是要彰显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要在人际关系上效法上帝的形象,我们的情感显明了人在本质上是需要关系的。我总不可能只为自己而活,他者总是存在的!只是为自己牟利的单一动机可以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破产,如巴西所出现的情况,甚至可能使更复杂的经济体系崩溃。复杂的体系需要“共治(panarchy)”原则[6],要传递目标,像脑部的神经细胞把人类恐惧的情绪交织在复杂的沟通系统中。同样地,人的贪婪和嫉妒显明了人的恐惧,经济体系因贪婪和嫉妒而崩溃,进入“无序状态”,变成不可预知、不可收拾的混乱状况。
很多时候,短浅的目光因“成功所带来的失败”而变得盲目,正如我们现在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意识到的情况一样。因为现代化以理性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以及民主来塑造我们今天的社会,当现代化的隐忧被重新评估时,这一切传承下来的观念都受到质疑[7]。如今,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城市化和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急速发展,每种情况都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至高无上的科学思维和无从反驳的赚钱逻辑既无法治疗人际关系中所受的伤害,也不能为社会伸张正义,除去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的现象。
因此,我们不但要问“我是谁”这个问题,而且不要成为一个“个人(individuals)”,而是成为一个“人(persons)”,意思是成为“为他者的自我”。这是圣经的命令——“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会在信息余下的部分中讲述“个人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历史,特别是美国人对“空无的大陆”的体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45-1647年英国内战之后颁布法令,宣布君王已被杀掉,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君主”。约翰·洛克(John Locke)则进一步下令,宣布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工作和产品的“所有者”,就如早期殖民为自己的新殖民地清理森林一样。接着,尚·雅克·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宣布,我们每个人都是“对自己的情绪自觉的人”,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8]难怪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观察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实验室,为“个人的兴起”这种新的人类现象进行试验。这种现象演变成当代的自恋心态,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9]。
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就国际广告代理商奥美公司(Ogilvy & Mather)的新政策写了一本书,名为《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如何预测市场新道德标准和建立有目标的企业/For Goodness Sake: How to Anticipate the New Ethics of the Marketplace and Build a Purpose Enterprise》。你也可以到大型书店中售卖商业书籍的部分,留意一些商业书籍书名的变化︰《人力方程式/The Human Equation》、《先问为什么?/Start with Why》、《目的经济/The Purpose Economy》、《以人为本的品牌/The Human Brand》、《修正游戏规则/Fixing the Game》、《团队的五大弊病/The Five Dysfunctions of a Team》、《友爱的公司/Firms of Endearment》、《欣赏式领导/Appreciative Leadership》、《情绪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些都是讲述商业文化如何经历剧变的书籍。正如阿瑟·佩奇协会(A. W. Page Society)2007年度的白皮书《真正企业/The Authentic Enterprise》中大胆指出的:
“今天,商界领袖更加需要成为整合者和沟通者,去推动错综复杂、非线性、全球化和分散管理的业务单位、功能和流程。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什么才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呢?就是真正的人性化,并且知道如何与别人建立互信。因此,现在的商业组织要问:‘我们在服务别人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企业的新目标,但并非市场销售的再思。我们只可以说我们需要“转化(metanoia)”,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考、生活和行事为人的方式。传统福音派称之为“重生”。但不知何故我们往往“胎死腹中”。商界呼吁企业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重新认清其存在的主要原因。这是世俗世界所谓的“看在老天的份上”,或基督徒圈子所说的“为基督的缘故”。然而,企业主管——即使是基督徒——却都在自我形象和企业形象这两个身份之间挣扎。不管是非信徒还是基督徒,把三者融为一体都需要“转化”。
正如我和我儿子所讨论的,“转化”有七种特质或表现:
⑴ 它是无边无际和意想不到的;
⑵ 它是超越理智的;
⑶ 它是难以理解地令人叹服的,如“一段新感情的推动力”一样;
⑷ 它所流露出的不一致性,源自最深切的信念;
⑸ 它寻求并建立与其他人更深层的关系;
⑹ 我们透过转化对自己的故事和身份有更充分的了解;
⑺ 我们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渴望促进它的转变。
然而,这一切特质都要存着谦卑的心去寻求和体现。所有成瘾行为,甚至九型人格测试所描述的那些成瘾行为,都需要靠谦卑和勇气才能克服。然而,这种情况在商业市场很罕见。正如汤姆森男爵(Lord Thompson of Fleet)这位著名报业大王所说:“谦卑!我不需要谦卑!如果我一直都谦卑,现在我会身处什么地位呢?”英国议院的天主教领袖朗福德勋爵(Lord Longford)曾在《谦卑/Humility》[10]这本小册子中引用这句话。他用自己的财产扶助弱智儿童,并一直以个人名义致力于改变社会文化对弱智儿童的态度。正如他的朋友范尼云(Jean Vanier)在加拿大所树立的典范,现在他正透过“方舟(L’Arche)”这个团体在世界各地开展事工。
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谦卑”使人摆脱自我意识,让人心里充满上帝的意识。上帝是谦卑的源头,祂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却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只能藉着上帝所赐的谦卑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勇气”是不管付上任何代价也要做正确的事。即使别人看来可能是荒谬的事,也愿意为此牺牲。去年,阿根廷有一名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年轻统计员揭发了国家已经破产的真相,这一举动需要勇气。然而,在一群年轻人的支持下,他胜过了自1930年代已侵入阿根廷政治的纳粹病毒。有一个来自亚马逊原始部落的女孩,名叫玛丽亚·达席尔瓦(Maria da Silva),她十六岁仍然目不识丁,却加入环保党派去“拯救亚马逊森林”,向巴西木材大王发出挑战。这一举动也需要勇气。后来她成为了第一位联邦环境部长。她更进一步反对她的支持者卢拉总统(刘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President LuLa, or Luiz Ignacio da Silva),揭露国家的腐败情况,这样做则需要更大的勇气。现在她成为了201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存着谦卑的心去作这一切,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在生活中寻求上帝,使自己更充分地意识到上帝的同在。曾经有几次有人要暗杀她,她请我为她祷告,有很多人也正在为她祷告——她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活下去,还是准备为自己的国家而死呢?
四、“我是谁?”——我在所属的家庭和企业关系中的身份。
我是一个生存在社会里的人,我需要群体关系,因为我需要“有所属”。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利用金钱去建立自我意义、自私的欲望,正如各种成瘾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根深蒂固的行为代代相传。一个家族企业、一个更大的企业,甚或一个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分别,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玛丽亚·达席尔瓦的生命。她行事为人像上帝的儿女,她完全的爱把惧怕除去了(约壹4:18)。而她自己也深深地经历到“转化”——从她身为一个亚马逊人所承继的一切,到成为一个属上帝的女人和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她明白到巴西唯有透过基督教伦理才能够恢复经济。
然而,世界被不良的家族企业所支配,农业和企业都是如此。圣经中浪子的比喻所说的情况不断在人类历史中发生,浪子与他的哥哥都是“失丧的”儿子。“我是谁?”我们可以从遗传、神话诗词、历史和当代等方面去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家庭问题没有好好处理,正如家庭和教会容让这些问题存在一样,企业便会崩溃。讽刺的是,企业能够突显这些不良的关系,没有别的机关能够如此揭露这种情况,并对此发出挑战。
五、知识不可能在良好营商方式中被“储存”起来而总不丧失。
可是,有多少东西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被“储存”起来了呢?在2世纪早期教会出现的第一个异端是“诺斯底主义”。早期教父在生活中把他们对使徒的回忆体现出来,坡旅甲(Polycarp)忆述他对使徒约翰的回忆对他童年所带来的影响。他预备好为这些改变他一生的回忆而死。殉道者以生命见证真理。我们的神学院却是“诺斯底知识”的来源,年青的基督徒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只要给我一点点知识,让我可以每周在关顾露宿者的志愿工作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反诺斯底主义”的举动,让上帝的话语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忆述他在八十年代末担任柯达公司(Kodak)商业顾问的经历。柯达的实验室充满天才横溢的人,这些天才发明了数码相机。柯达公司的创办人伊士曼(Eastman)却因傲慢自大(hubris)而无法摆脱自己从前的新发明——银卤化物的提炼。这项发明令柯达(柯达是美国北达科他州的缩写,这位化学家曾在那里居住)成为了胶卷技术的全球领导者。这个领导地位却从这位隐蔽的化学家身上被夺去。把柯达公司摧毁的,不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而是公司的股东。后来伊士曼自杀身亡。柯达公司的科学家多年来一直恳求伊士曼发布他们的新知识,却无济于事。
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例子说明了“储存的知识“所带来的恶果,我们也可能因傲慢自大而把神学知识储存起来。我十分钦佩一位新加坡的英雄,他也是维真神学院的校友。他是一名医生,他没有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储存起来,而是运用这些知识在一些地方服事,帮助当地政府在这个面积甚广的地区开设诊所。他以牺牲舍己的精神运用医学知识去服事,因此被誉为“那里的朋友”。这向我发出挑战,让我深思如何体现自己恒常的公众演说。这是以微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当我正在预备远东之旅的各篇讲章时,人们却来叩门要求我帮忙,我如何存着忍耐的心去回应呢?我们每天在时间安排上的张力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我聆听和照顾孩子的时间是否比我在事工上所摆上的时间少?我可曾为“谁是我的邻舍”下定义?福音的体现是无穷无尽和不可名状的,却必须透过个人日常生活态度和行为而实现出来。
六、全球企业跨越文化在互信中团结起来。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跨越文化联结起来去表明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维真神学院学习时有幸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七十年代早期,人们常常问为什么选择温哥华。当我们面对二十世纪的大西洋,我们可能会选择利物浦去面向大西洋,从美国工业革命中获益。但现在来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在环太平洋地区面对着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你们在新加坡也需要相同的全球视野。
基督信仰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不得不分阶段展开宣教旅程,最后当他到了罗马城的时候,才能够面向整个罗马帝国。然后,他开展重大的牧养工作,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被自己的民族意识所蒙蔽。有些人仍然被殖民地意识蒙蔽,以为基督信仰源自优越的西方文化。年初,我在日本向日本的基督徒指出他们接受福音时所面对在文化上的主要障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傲慢自大;相反,日本人拥有很多美好的特质,值得西方基督徒欣赏、接纳,并融入信仰中,使基督信仰更丰富地体现出来。现在我察觉到最原始的文化也有我们需要普遍接受的道德素质。
世界贸易正面对同质化的危险,但它对于接纳多元文化有很强的适应力。其接纳的速度与基督徒的缓慢改变形成强烈对比。
七、新加坡人所提出的技术问题:如何可以做到?
最后,有人建议我必须解答新加坡听众最喜欢提出的问题:“如何可以做到?”我们就以这个实际的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吧。可是,我的响应也许有点出乎意料:
1、透过促进基督徒生活的全球视野。这一点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讨论过了。
2、透过除去本地基督教群体的狭隘视野。这一点比较难做到,因为这些习惯(habitus)可能需要思想上的改变。这种情况在历史悠久的教会尤其显著,有牧者曾经把这几十年来被发现后又隐藏起来的人口密集小区联结起来吗?
3、不要问“如何”,而是问“谁”!
这就像森林里的农夫选择住在自制的茅棚里,而不住在万王之王的宫殿里一样。傲慢自大地以为自己知道“如何可以做到”,只会产生“错误的自我观念”。技术上的知识永远无法取代人际关系上的知识。因此,我们要谦卑下来,心里充满基督的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
专业人士往往讲求实效,因自己的坚定而引以为傲。但基督徒应是受托付、视野广阔和值得信赖的,而且能够强而有力地把过去和未来整合起来。基督徒领袖的逻辑思维并不像管理思维那样是操作式的,因为它察觉到“人类”的复杂性,并不受制于非人性化的科技,正如我的同工纪克之所探讨的,而且它拥有一个指南针给未来指引方向。基督徒领袖的思维应摆脱抽象的领域,使事物具体化和个人化,并把迫切与超卓融合起来。
今天,世俗主义者对所有宗教用语存着偏见,甚至反对教会及其历史。但明智的基督教商界领袖可以运用精湛的商业原则去激起敌对者的兴趣,让这些世俗受众意识到他提出的是崭新的人类见解,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他如何获得这些见解。我曾提到我的儿子如何以三位一体的奥秘这一神学概念去建议企业主管如何“推广品牌”,并举例说明主管的身份是“为他者的自我”。
戴维·赫斯特(David K. Hurst)是一位基督徒生物学家,他在其著作《领导新生态/The New Ecology of Leadership》中讨论了另一个例子。[11]他公开引用希伯来文圣经去建立一个“生态循环”图,以旧约圣经中“旷野”的主题去描述行政人员如何陷入权力所带来的困惑中;以“山”的主题去激发创新领导者的思维;并且以“应许之地”和更新的群体的主题去指出明智的选择让其创新者产生信任。
他描述了一间公司面对双重危险,陷入不断改变的“漩涡(旷野)”中,这是指“权力”;离开“应许之地”,这是指信任领导者的管理技能,这是成功和才能的陷阱、过度稳定的“绊脚石”。这两个陷阱中间是“甜蜜地带”,创新的领导和策略管理就在这里把经理和领袖们团结为一个团队。这既不是留在过去,也不是梦想未来,而是活在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存留的当下。
这令人不禁想起十七世纪奥秘派的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和高萨德(Jean Pierre de Caussade)所谓的“此时此刻的圣礼”。基督徒社会心理学家西蒙内·舒纳尔(Dr Simone Schnall)和他的同工观察这种心灵的提升如何促进利他行为。看见别人的善举和自我牺牲的行为会引起心灵提升的感觉。这些利他行为让别人模效,使利他主义实实在在地增长[12]。他们在往后的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指出,“道德的提升使道德价值变为行动”[13]。
多年前,C. S. 路易斯的同事、政治学家泰勒(A. J. B. Taylor)曾说:“大事皆因小事起。”不仅在政治领域中如此,同样地,在商业领域中,领导者因他们利他的生活方式而得到信任,并因为只顾自身利益而得不到信任。要成为“为他者的自我”,这个身份是关键所在,这表现出同理心、能够明白和分担别人的感受。当领导者体现这些人类价值,并得到信任,国际贸易便得以维持。
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在他的短篇作品《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The Fate of Man in the Modern World》中写道:
“……在古代结束之时,基督教是进入世界的一股崭新和年轻的力量;但现在,基督教在人类岁月中变得古老,并背负着悠久历史,基督徒在当中犯罪,也背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们必定看到对历史的审判也是对基督教在历史中的审判。”
最近,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断言:“基督教已死”,却补充说:“但基督仍然活着!”是的,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快要死去。但现在基督徒商界领袖要扮演一个奇妙的角色,基督徒群体应当加以极力培育和鼓励。然而,基督徒商界领袖的角色与保罗以制造帐棚为业的角色并没有分别。保罗以制造帐棚为业,在罗马帝国的路上往来贸易,作主的仆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基督徒群体却仍然不断以狭隘的视野去蒙蔽自己眼睛,对他们来说,这个时代的全球视野看来几乎是超现实的。让我们恳求主除去我们被蒙蔽的眼睛,在“当下”为基督而活。阿们。
[1] C. S. Lewis, The Last Battle, (New York: Harper & Collins, 1956), 200, 204-205.
[2] Horst J. Helle所引述,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2015) , 79
[3] Dirk Evers et alii, ed. Issues in Science and Theology: Do Emotions Shape the World?,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6
[4] Philip Cushman, Constructing the Self, Constructing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s, 1995)
[5] 参Jorgen Bukdahl, Soren Kierkegaard & the Common Man, revised, trans., Bruce H. Kirmmse,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1).
[6] Lance H. Gunderson & C.S. Holling,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2002
[7] Charles Taylor, The Malaise of the Modern, CBC Massey Lecture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td., 2012).
[8] 卢梭(Rousseau)的小说《爱弥儿/ Emile》描述了一个沉冤的孩子的感受,引致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9] 有很多关于自恋文化的研究,但以医学角度作概要的有Alexander Lowen, Narcissism: Denial of the True Self,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Simon & Schuster, 1985
[10] Lord Longford, Humility,
[11] David K. Hurst, The New Ecology of Leadership, (New York: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2012)
[12] Simone Schnall, Jean Roper, and Daniel M.T. Fessler, “Elevation leads to Altruistic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2010, 315-20
[13] Simone Schnall and Jean Roper, “Elevation Puts Moral Values into Ac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3), 2012, 373-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