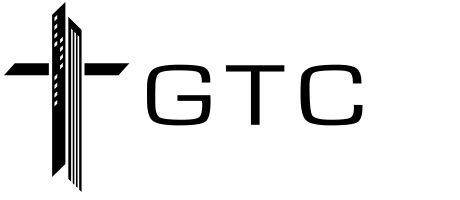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在政治上的分立,这一观念几乎仅仅源自基督教传统。在耶稣被质问犹太人是否应当向罗马政府纳税时,基督说了这句著名的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是基督教政教分立思想的源头,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及改教时期路德的“两国论”[1]中,逐渐清晰了相关圣经教导及历史性的应用。并在加尔文和改革宗神学中,在圣约历史与基督国度的世界观下,高屋建瓴地奠定了“政教分立”的神学依据。之后随着清教徒运动,在英、美等国逐步形成了消极的和世俗的政教分立的国家理论[2]。有学者评论道,“在中世纪有两个特独的政治原则的遗产,第一是政教分立,第二是政府权力的神圣性”[3]。
这句经文的前半段,承认了“凯撒”所指代的世俗权力的正当性。初代教父们据此认为王权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于上帝的托付和设立。对这一世俗权柄之神圣源泉的强调,影响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扩展及偏差。而上帝藉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1-7的启示,是对基督这句教训最好的注释。在理解圣经对属灵、属世两个国度、两种权柄之关系上,在整本圣经中具有提纲挈领的地位。其中要求信徒顺服世俗君主之权力的段落,在教会和世俗政府的历史上,也常被扭曲和误解。有学者评论说,“对各国政府而言,这大概是圣经中最中听的经文之一。”[4]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1-7)
主耶稣所言“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导向了在近代被称为“政教分立”的国家观,其中包含了精神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属灵国度高于世俗国度的宇宙观场景。而罗马书的上述经文,则为世俗权柄设立了“应当如此”的公义准则,可以视为托付、代理及审问之条件。
统治权是神圣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24:1)。换言之,承认统治权的神圣性,其实质是承认上帝主权的圆满和普遍。即上帝之荣耀,投射和覆盖了包括世俗权柄在内的宇宙场域。就像一滴水彰显太阳的光芒,当任何一个人,有权吩咐、命令、请求另一个人作某事或不作某事时,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上帝对世界事务的精确干预,即上帝藉着万事对这个世界的“吩咐”。我们若听从另一个人(君王、官员、父母、牧师、上司、兄长等)而来的吩咐、命令和请求,我们听从的都是那位发号施令的上帝。在救赎的历史中,具体来说,就是听从那位从死里复活、坐在超越时间、空间之荣耀宝座上的大君王[5]。
罗马书13章所承认的统治权之神圣性,并不在上帝创造、护理和审问的权柄之外。这意味着,其一,一旦承认统治权的神圣性,也就承认了统治权在本质上是被约束的。其二,一旦承认统治权的神圣性,就等于承认上帝是合法性的源头,而强权不是合法性的源头[6]。这是对任何意义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或“这个世界要靠实力说话”的国家观的彻底否定。换言之,这不是对专制的合法性论证,恰恰是对宪政的合法性论证。
一旦承认了统治权在本质上的被约束,就意味着统治权同时也是世俗的。世俗权柄的神圣是一种渊源上的神圣,一种从代理人指向被代理人的神圣。或一种因顺从而来的神圣。因为“神圣”的意思,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参出28:36,32:29,利27:21),凡物归耶和华为圣,凡物就是神圣的。对上帝的子民而言,则是因着信心而“成为圣洁”[7](在这里指分别为圣,相当于称义)。就如摩西所举起的牧羊人的“杖”的神圣性质。最后,当这根杖被放入约柜,这种被赋予的神圣性亦被封存,成为预表性的、约的记念。换言之,统治权的神圣,是一种因被上帝使用而带来的顺从的或消极的意义上的神圣,而不是自身属性上的、实际权力之范围和行动之自由的神圣。
承认统治权的神圣性,反倒带来对统治权的限制的开始,意味着死而复活的基督在国家事务上收复了失地。由此,罗马书13章在承认世俗权柄之“神圣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世俗权柄自身的、任何意义上的“神性”。在国家观上,保罗的神学与旧约众先知的神学是一致的,即圣经从来没有将普世的政权视为上帝国之外的另一个领地,或将君王的权柄视为与救恩无关的、另一种自足的权柄。故此,在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欧洲,教会在历史上有效地阻挡了君主(或政府)在政治哲学上登上更高的位置,即对国家主义的偶像膜拜[8]。
但从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教会在欧洲的衰落,全权主义的、古罗马式的国家主义观念,开始脱离罗马书13章的托付和限制而兴起。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在一种整全性的国家主义观念中,必有一个最高的位置。任何政体都必须解决“最高权威的个人归属问题”。他称为“Herr”,泛指上帝、天子或皇帝。近代思想史和国家史的一个明显脉络是,在改革宗神学影响下的世俗政权中,从未形成过整全性的国家主义观念及其政治实践。而在天主教、东正教和路德宗影响下的世俗政权中,却不断涌现出全权主义的国家主义蓝图及其政治实践。或者说,在改革宗神学影响下的国家,最终形成了“政教分立”的国家模式,并将“宗教自由”视为宪法意义上的第一自由。而在改革宗神学未占主流地位的国家,却未形成、迄今也未完全接受“政教分立”的国家观,也未将“宗教自由”上升为一个关乎国家之蓝图的根本性原则。
因为加尔文主义对荣耀上帝之圆满主权的崇拜,破碎了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国家观念,否定了世俗政体及其政治哲学中的、任何意义上的“天子”。英国和美国的立宪史表明,只有在这种破碎中才会产生出近代立宪的概念。
因此,笔者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这一受到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宪政理念,译为“政教分立”。而将以法国为代表的、以无神论的或反宗教为倾向的、力图将信仰逐出狭义之政治乃至广义之公共领域的国家主义观念,称为“政教分离”[9]。
加尔文在对罗马书13章的注释中说,“我们顺服不是因为他们有权柄可以刑罚我们,我们顺服是因为神的话与良心而来的自愿的顺服”。他强调说,保罗在“这里的论点完全是关于民治政府的,因此若有人利用人的良心或本节经文来建立他们独裁的统治,是没有根据的”[10]。
加尔文的这一国家-教会观,得到之后的圣约神学家们的认同和发展。并在参加了威斯敏斯特会议的神学家、苏格兰的卢瑟福(1600-1661)那里,获得了实践的应用。卢瑟福在他的名著《法律为王》[11]中,引用罗马书13:1-7,认为统治者的权柄来自上帝的托付和设立,但这一设立乃是通过人民之同意予以印证;同时,统治者亦有责任按着上帝的诫命和要求行事。如同加尔文一样,卢瑟福引用了许多旧约经文来证明这一国家-教会关系的模式[12]。他的这本书,成为对加尔文主义“政教分立”观的经典阐释,对清教徒革命影响巨大。
20世纪初叶,卡尔·巴特对罗马书13章的注释曾引起极大争议。鉴于几个原因,笔者将他的注释引用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其一,巴特继承了德国的改革宗神学,因此就教会传统而言,他站在欧陆与英美之间。其二,巴特在纳粹兴起的关口,出于近代国家主义灾难的最高峰,因此就历史而言,他站在路德的国家论与希特勒的国家论之间[13]。其三,巴特反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自由派神学,但他仍深受德语思想资源的影响,未曾向着宗教改革“惟独圣经”的立场完全归正,因此就神学传统而言,他站在自由派神学和改革宗神学之间。但他的神学观念对20世纪的欧洲教会和国家都具有极大影响。就历史的观察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巴特将现存的人类秩序,包括国家、教会、社会、家庭的总体设为:
(a.b.c.d)。
而将上帝的主权秩序对这一总体的扬弃(不效法这世界)设为括号前的负号:
-(+a+b+c+d)。
他认为,人间的革命或反抗再彻底,也不能视为括号前对人间秩序之总体的全面扬弃,也就是不能被视为那个“神性的负号”。最大的成功,可能只是扬弃了括号内的现存秩序,也就是把现存秩序的正号变成了负号,于是他得出下列公式:
-(-a-b-c-d)。
显然,括号前那个神性的负号,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象征,会辩证的、出乎意料地,将人们擅自以革命方式改革的负号重新翻转为正号。这意味着任何革命都只是一种不考虑神-人关系的、建造巴别塔的面子工程。换言之,革国家的命,在本质上依然是国家主义的。如席勒的诗句,“他信心十足的将手伸向苍穹去取下他永恒的权利——这权利本来宛如星辰,不可转让,坚不可摧的挂在天上”。巴特说,君王的权柄是有界限的,“但他们信心十足伸向天际的手却不为自己设立界限”。如果将神与人的关系考虑进来,巴特认为,旧事物必定会在革命的算法之后卷土重来,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特的这一公式,可谓对20世纪人类历史的精当而概况的描述。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文化革命,乃至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的结果,都是“反叛者通过反叛站在了现存事物的一边”。因此,巴特认为,政教分立对教会而言,意味着一种消极的和防守型的政治哲学[14]。“意味着不发怒,不推翻”,而将美善的希望放在传扬和顺服基督的爱上,放在更高的权柄和国度上,而不是放在政治国家的场景之内。这看似一种后撤和放弃,其实是对政治国家之“神性”的最大程度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令任何国家主义者勃然大怒的、真正的“激进”立场。但唯有当教会坚守了这种立场时,教会对社会的挑战、影响和祝福,才是福音的,而不是革命的;是十字架的,而不是奋锐党人的。
当信徒对基督的忠诚和对君王(国家)的忠诚发生冲突时,就像古希腊的安提戈涅一样,需要基督徒的良心作出抉择。这也是为什么清教徒运动在罗马书第13章之上,发展出对“良心自由”的强调[15]。如果夸大了对在上掌权者的服从,就会取消信徒“心中的天国”[16]对世俗权力的、来自上帝主权和诫命的审视。换言之,仅仅“因为刑罚”,而不是“因为良心”的服从,将夺走基督徒对独一上帝的崇拜,而将这种崇拜归给人间的掌权者。这也是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在历史处境中反对和远离“三自”路线的主要原因[17]。
因此,教父奥古斯丁承认,“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时,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不服从的态度。”[18]他藉着对罗马帝国之覆没的解释,完善了教会对罗马书第13章的认识,凸显了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在末世中的对立和重叠。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布27条《教皇敕令》,宣示教皇有废黜主教和国王、任命圣职和制定法律等权利,并随之废黜了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法学家伯尔曼将围绕这一敕令的冲突称为“教皇革命”,视之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六次革命之首[19]。因为这一“革命”导致了宗教管辖权和世俗管辖权的分立,使基督教的“政教分立”模式成为欧洲的制度遗产。从此,某种程度的、这种或那种的“政教分立”观成为欧美国家观念的主要渊源,也成为近代立宪政体兴起的一个历史地基。
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亦是这一思想最重要的辩护者。他对罗马书13章的注释,更看重圣经对世俗权柄所提出的公义准则,进一步将消极的不服从立场推至对暴政的抗拒。他说,“一位国王如果不忠于其职守,他便放弃了要求服从的权力。废黜他便不是叛乱,因为他本人才是叛乱分子,人民有权予以镇压。”[20]到1302年,教皇在《一圣通谕》中再次确立了属灵权柄高于世俗权柄的主张[21],标志着二元论的国家模式的获胜。
这种“两国论”的、政教分立的原则,是防止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偶像的解毒剂。它将人类对整个宇宙和历史的理解,搭建在同一位创造之神和救赎之神对时间和空间的全权掌管之上。但是,阿奎那以降的思路,也包含着中世纪教会积极改造、乃至控制世俗政治的政教合一的趋势,将教会属灵权柄在性质上对国家的审视和涵盖,落实为历史实践中对国家权柄的介入和干预。二千年的教会史显明,基督教一旦偏离了对上帝主权式的恩典的信仰和崇拜,就会对罗马书13章的解释失去平衡,背弃“政教分立”的原则。对属灵权柄的高举,也可能成为与极权主义最彻底的混同。在改教时期,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皇对属灵权威的扩大和把持。他限制了阿奎那的思路,重新回到奥古斯丁对罗马书13章关于顺服及其限度的基本立场。在《关于世俗权力:对它的顺服应到什么程度》一文中,路德重申了“政教分立”的立场:
亚当的后裔被分为两部分,就如上文所讨论过的。一是在基督治理下的神的国度,一是在政府治理下的地上的国度,两者都有自己的法律。若没有法律,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存活。政府的法律无非是涉及人的身体、物品和地上外表的事。至于灵魂,上帝不能也不允许任何人去治理,除了祂自己以外。所以当政府把治理灵魂揽为己任时,它就越权,侵犯了神的治理[22]。
这一基本立场,就是福音(或人类的永恒福址)与国家无关。教会传扬福音的使命,来自基督天上地上至高的权柄。第一,这一权柄不能被理解为置于国家的治理之下,否则就应如使徒彼得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路德强调说:“如果世上有权的人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的话,就没有必要这样说了。”这也是使徒行传在其开放性的结尾所强调的,三十年的初代教会史的实践证明了,“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徒28:31)第二,教会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主动借助国家的强制力(这并不否定上帝有主权和自由随己意使用国家作为扩展福音和国度的工具[23])。一方面如奥古斯丁所说:“信是白白的,没有人可以被强迫违反自己的意志去相信什么,也不应该被强迫。”[24]另一方面,“使用武力永远也不能禁止异端,异端是属灵的事,它不能被铁器击垮,不能被火焚烧,也不能被水淹没。惟靠神的话可以征服。”[25]在为信仰争辩和传扬人类的永恒福址上,使用任何行政的强制都是对“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2:2)的否定。如果强制力是被托付给教会的,又何必等到今日,何必轮到我们来逞血气。罗马书13章对统治权的描述,是对人类思想史上各种国家理论的最不留情面的否认。从未有过某种价值的正当性,如圣经的启示如此强大和自足,却又完全自外于国家,并把国家拆迁安置在一个整全的宇宙场景中。在路德和加尔文那里,国家仅仅被视为一种寻求基本和平的政治合作方式。在基督徒中,原本不需要法律和政府。只是这世界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存的世界,世上有一人不是基督徒,人类就被授权活在“政教分立”的模式下,需要顺服世间的法律,不能依福音进行肉身的统治,而把肉身的审判留给对基督再来的、永世的盼望。否则,“就像把狼、狮子、鸽子和羊放牧在一个圈栏里。”[26]
在《劝基督徒毋从事叛乱书》[27]中,路德指称教皇制度是邪恶的魔鬼撒旦的代理人。但他同样反对再洗礼派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观,及针对国家的叛乱。他认为这些叛乱同样是“出于魔鬼的建议”,是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诱惑。路德引用“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参申32:35,罗12:9)的经文,为“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这一法治原则提供了神学上的解释。他认为“叛乱无非就是给自己做审判官,作伸冤的”[28]。如果依循人间的法治,人与人可以互做法官,人间的审判权是在程序正义之下的“换手抠背”。但是,一旦否定了法治,即否定了上帝对国家的授权,就等于拒绝任何人来作自己一案的法官。因此革命的实质就是自我伸冤,废除一切来自他人的吩咐、命名和请求。因为革命不相信在这些“他人的吩咐、命名和请求”之上,上帝仍有主权、荣耀和恩典。换言之,革命的实质就是公然宣布上帝国的沦陷,公然声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失败,或矢口否认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了教会。
因此,在路德看来,革命革掉的不是他人的命,革掉的是上帝“伸冤在我”的至高的和最后的主权。换言之,任何叛乱都是对上帝的叛乱。面对不公义的现实,路德认为教会只有三件事可以做,应当做。一是承认并除去自己的罪,否则“你们向天上所投的石头,要落在自己头上”。二是卑谦的祷告,“为那城求平安。”(耶29:29)三是宣讲和写作,“以你们的口为基督的口”,使谎言被揭露,使真理被传扬,使教皇制度“在全世界面前蒙羞”。路德相信,一切灵魂的罪都“非因人手而灭亡”,而是如保罗所说,“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帖前2:8)
路德坚信神的话语的力量是一种信实的力量,因为“诸世界是籍着神话造成的(来11:3)”,因此他将对人的传讲和对神的祷告,视为基督徒承受苦难、改变社会的最重要的、甚至也是唯一的方式[29]。这和英国古典立宪主义一直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视为经典的自由概念是一致的。暴力是世上最简单有效的威权,也是肉眼可见的、对人与人的一切关系的最大诱惑。没有一种与暴力彻底相反的好消息,很难想象这种对强权的驯服在人类历史上的展开[30]。
但对加尔文,尤其是对后来的约翰·诺克斯等改革宗神学家来说,路德还是过于强调了对国家的顺从。加尔文对罗马书13章的立场,为教会奠定了一种立宪主义的实践道路。如果掌权者违背或滥用世间的法律,“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将意味着什么呢?是顺服那些违背法律的行为,还是顺服那些被违背了的法律?从这里,可以看到由罗马书13:1-7对世俗权柄的敬重与顺服,与伯尔曼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是一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基督徒基于一种来自更高权柄和更完整之宇宙场景的启示,而不是基于对世俗法律及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而养成了对统治权的顺服。这是现代立宪主义和“政教分立”的国家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离开了这种顺服,世俗法律就真是形同虚设了。这一新教的政治伦理,为立宪主义的扩展和英美普通法传统下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世界观的蓝图和路径依赖。在教会对世俗权柄的不服从上,由阿奎那式的以牙还牙的政教争夺模式,转向了从加尔文到马丁·路德·金的,从诺克斯到王明道的,以“宣讲、写作、辩论、诉讼”为手段的、“非暴力不服从”的法治模式。
只有一种“绝对的和彻底的有神论”(参:伯特纳论加尔文主义),才能破除对任何世俗权威的偶像崇拜。如“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所言:
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出20:3-4)
反对偶像崇拜,与政教分立的精神是一致的。换言之,一个缺乏“政教分立”的国家,无法在政治上免于拜偶像的罪。即使福音书没有记载基督那句醒目的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一个神圣的国家”这个命题本身也是极端亵渎和自相矛盾的。从历史上看,教会抑制了国家主义的膨胀,为制衡国家权力的立宪道路开辟了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东方专制主义的“神权”统治下是缺乏的。凡多神教、泛神论或辩证唯物论盛行的地域,几乎都是极权主义政治的温床。
政教分立的原则,已暗含了对国家的、在先的(或预定的)价值约束,也暗含了对唯意志论的民主(或大多数人)崇拜的反对。一个“政教分立”的政体,不可能同时是民主至上的政体。因为政教分立和民主至上也是反义词。承认政教分立,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意志,或多数人的意志都只是一种世俗的、被授予的和第二位的权威,不可能因其质量或数量而上升为一种全权。
17世纪中期的清教徒运动中,克伦威尔手下的激进派废除王权、处死国王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菲尔默,发表了《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利》,坚持国家的统治权柄都来源于上帝对亚当的授权。在对罗马书第13章的解释上,持一种近似于路德的立场。约翰·洛克幼年时,正值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他的《政府论》深受清教徒神学的影响,他以契约论这一世俗化的论证,取代了圣约神学观,尽管契约论仍受到圣约神学的影响和启发[31]。洛克的反驳,使菲尔默几乎成为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坚持“君权神授”立场的最后一个著名人物。在近代以后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也几乎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
菲尔默坚持基督徒的“生而顺服”,他反对当时盛行的“生而自由”的政治理论,认为如果要终结近代以来的叛乱,必须要否定这样的理论。他如此描述这种自由主义理论[32]:
人类生而就被赋予了免除一切服从的自由,人类自由的选择的他所喜欢的政府形式,任何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最初都是由根据人类多数的自由选择所给予的人类权利来决定的;因此,国王们要服从其臣民的责难和剥夺。
在反对唯意志论的立法权和创制权,质疑国家主义和民意的崇拜上,菲尔默的保守主义立场,其实更接近改革宗神学对罗马书13章的理解。不过,菲尔默对民治政府的某种深刻的敌视,却是路德和加尔文也不能赞同的。菲尔默挖空心思地论证英王是亚当的直系后裔,因而对他的臣民具有神圣的统治权柄。这是对圣约观念的一种犹太式的,或律法主义的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尔默的立场的确落后于改教运动和清教徒的观念,不可能扭转“政教分立”之立宪国家的转型。
洛克与菲尔默之间的这场辩论,是圣约世界观的清教徒思想,向着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政治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折。洛克比霍布斯退得更远,他不再承认圣经或上帝的主权托付,是现实的世俗权力的神圣来源。他将政治的基础“革命性”地建立在了自然权利和世俗化的社会契约论上,即将对基督国度的信仰排除在了对政治和国家模式的论证之外。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自由主义的“政教分离”模式,日益将信仰视为私人生活而已。在洛克这里,上帝的超验正义变成了人类的意志论的“自然权利”。国家在起源上因为割断了来自上帝的代表权柄而更加世俗化了。洛克的契约论从人性的恶与不可靠出发推演,用休谟的话说:“政治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无赖。”[33]国家权力的确因此成为一种工具性的权力,它甚至不能单独支撑起法律的正当性,与任何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更是相去甚远了。但是,这种仅仅承认和提防人性之恶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仍然是一种律法主义。因为它否认了教会在国家场景中的地位,驱逐了公民的宗教自由在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也就拒绝了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说,人在哪里拒绝了上帝的主权,就在哪里拒绝了上帝的恩典。
在美国建国初期,加尔文和清教徒的“政教分立”观,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教分离”观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宪法第一修正案》[34]。在法国,从洛克到卢梭的“政教分离”观,形成了反宗教的、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原则所构建的国家模式,不是一个“恩典之约”下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行为之约”下的国家。换言之,是一个落在咒诅之下的、偶像的国家,而不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所认信的、一个政教分立的、敬畏上帝的国家[35]。
最后,笔者以美国长老会总会于1788年修订、1789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3章第3条[36],作为本文的结束。长老会在这一修订版中表达了加尔文主义应用于当代社会的“政教分立”观,及对罗马书13:1-7的神学立场。一方面,教会与国家、属灵权柄与世俗权柄的实践运作、福音的能力与民事的强制力,被区分了开来。另一方面,国家之于教会、统治权之于福音信仰,仍被认为被上帝托付和追问了“如保育之父”的责任(参赛49:23)。这一改革宗立场的“政教分立”教义的出台与实践,比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俗称权利法案)早了两年(后者于1789年9月25日提案,1791年12月15日批准)。事实上,美国长老会总会对《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3章3条的修订版,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神学蓝本,在第一修正案中,教会与国家,两个不同的国度跃然纸上[37]。
国家官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代下26:18),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太16:19;林前4:1-2),亦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约18:36;玛2:7;徒5:29)。然而国家官员如同保育之父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份的各方面,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赛49:23)。并且,耶稣基督在祂的教会中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它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作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利的行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诗105:15;徒18:14-16)。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致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侮辱、暴力、诅骂和伤害;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撒下23:3,提前2:1,罗13:4))。
在当代中国,洛克式的契约论和法国式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模式,对未来的国家-教会关系,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和宗教观,乃至对中国教会、牧师和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国家观的影响,就目前而言,都远甚于圣约神学下的“政教分立”的国家模式。中国家庭教会对罗马书13章的解释,也更接近于法国式“政教分离”的观念(以及再洗礼派的分离主义传统),“三自会”更是极深地沦陷于对国家主义的膜拜。为此,这一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心中。也是笔者撰写此文,以有限的阅读、思考和梳理对当代中国这一重大神学及公共议题作初步探究的原因。
- 对改教运动之圣约和国度观念的描述,可参见笔者《圣约和国度下的自由》,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译后记,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 参见前注《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另可参考:约翰·维特,《权利的变革:早期加尔文教中的法律、宗教与人权》,苗文龙、袁瑜琤、刘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131。
-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魏育青译,张贤勇导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启示录5:13,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 刘同苏,《罗马书13章1-7节释义:圣经中反合性的宪政理论》,http://www.liutongsu.net/?p=85。刘牧师认为这段经文表明“是法统而不是强力构成了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服从,不是因为政治权力握有强力,而是因为政治权力的法统渊源(神所授予)。
- 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祂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 以赛亚书14:14,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 笔者曾于2006年10-11月应法国外交部邀请,赴法考察法国之政教关系,对这一欧陆式的“政教分离”观的思考,见笔者未刊文稿。亦可参见笔者对法国“头巾法案”的评论,《阿尔玛的头巾和莉莲的国旗》,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0月1日,http://news.sina.com.cn/w/2004-10-01/15024477823.shtml。
- 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论政府》,“公法译丛”,吴玲玲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131。
-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卷《不列颠宗教改革思潮》,第六部《反抗的原则》,此书将卢瑟福的书名译为《法律至上论》,笔者在《自由的崛起》一书中将之译为《法律为王》。
- 如:撒母耳记上12:1,撒母耳记下16:18,士师记8:22,9:6,列王记下14:21,历代记下23:3等。
- 路德的“两国论”因为缺乏圣约神学的整全框架,加之众多历史性的因素,形成了路德宗教会对国家的顺从和依附的传统,因此直到二战之前的德国,并没有确立完整的“政教分立”的原则。有学者指出,路德的国家-教会观,至少为现代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兴起,留下了世界观的余地。
-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 432—34。
- 参:罗宾逊·亨利(Henry Robinson,1605-1664)的《良心自由论》(Liberty of Conscience),《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卷《不列颠宗教改革思潮》。
- 参:路加福音17:21,“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
- 王怡、金天明等,《我们的家庭教会立场》,(秋雨之福教会印制,2010)。
- 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19。
-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14-16。
-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61。
-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Salvo Mastellone),《欧洲政治思想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45。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吴玲玲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2。
- 如旧约时代,耶和华对古列王、亚哈随鲁王等外邦君王及对波斯、巴比伦等外邦国家的主权性的使用。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象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25。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30。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10。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54。
- 马丁路德、加尔文,《论政府》,58。
- 如路德引用的以赛亚书11:4,“他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 如路德喜欢引用的哥林多后书10:4,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 参见笔者基于圣约神学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分析。王怡,《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第四章“宪政与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 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石楠、张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
- 休谟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而非超验的上帝圣约的角度,反对契约论,对契约论的唯意志论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如果不以圣约神学为出发点,人间的契约论的确就如休谟所说,是“虚构的”。参见笔者《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第四章,“宪政与约”。
- 因此在美国的宪法史和当代社会中,加尔文主义的“政教分立”观,与洛克式的“政教分立”观的冲突和争夺,一直在继续。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福音派基督徒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在总统的信仰表达、校园内祷告、法院的十诫碑等宪法案件和公共议题上的争议,都体现了这一基本的世界观的张力。
- 一些福音派学者过于强调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改革宗的圣约神学之间的渊源,但对洛克的契约论的世界观与改革宗神学的圣约世界观之间的巨大和本质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美国当代政教关系的诸多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思考。包括笔者译的《自由的崛起》一书,及约翰艾兹默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李婉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林集章牧师,《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第二十三章《论国家官员》,张敏颖译,王志勇编校(改革宗出版社,2010)。
- 约翰埃兹默《基督教法律顾问》,(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1984)。埃兹默用了三百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第一修正案的背景、形成和意义,揭示其正是上帝圆满主权之下的“两个国度”观的体现,是“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